
说起地方志,我的思绪回到20年前,那个光线昏暗、冷清寂静的档案室。那是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整理的是一个单位累积了30多年的档案材料。近三年的时间里,我日夜独自待在偌大的室内,在那些泛黄积尘的卷卷册册中分类、整理、装订、入册……一列列、一架架、一柜柜……我埋头于兰台旧籍,沉浸于一隅,甚至有点恍若隔世之感。没人交流,面对的是毫无生气的故纸堆。这样的工作也许是枯燥沉闷的。于是这个时候,翻阅室内图书架上的地方志书,成了我那时候放松、解乏、调节的方式。也就是那时候,我才知道,什么是地方志,地方志原来是那么丰富。这为初到这座城市的我打开了一扇了解地情的窗。
时间如细沙在不经意间从指间悄然滑落。架上的《肇庆市志》《肇庆大事记》《肇庆年鉴》……那砖头般厚的志书,也随着架上不断增多的档案卷册,被我慢慢翻阅过去了。
也许是那几年难得的静心读志,那不知不觉间的沉淀,我的积累也随着工作、生活、阅历日渐丰盈起来,所感所悟投注于笔端,便形成了一篇篇作品。这些作品多是在西江畔这座城市行走、观察和思考而写下的,于是不可避免地沾染上此地的风情,也是我人生中阶段性的记录。这些都与过去和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紧密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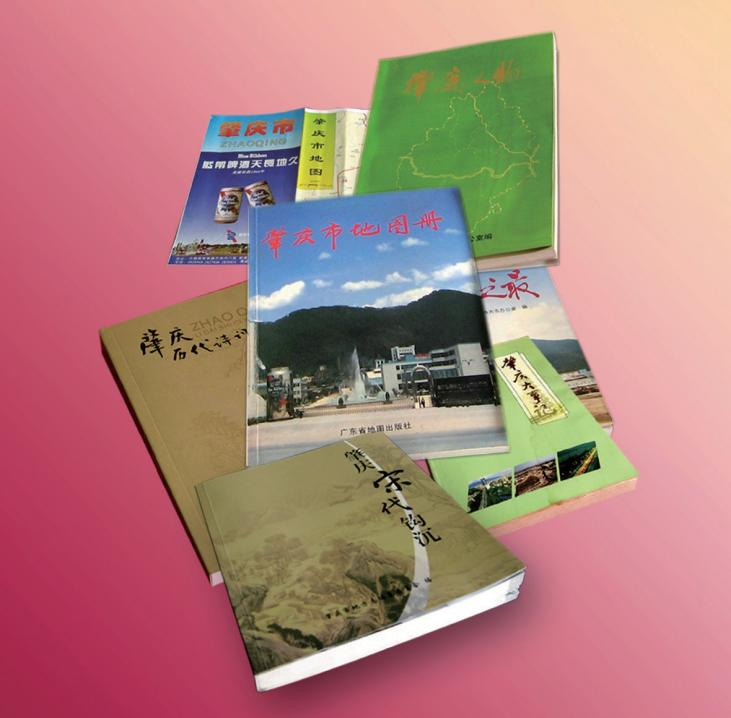
肇庆市地方志办出版的地情书籍(摄影:陈伟雄)
志书如河流,承载着山河的喟叹。志书中的笔墨,也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让人汲取前人智慧。翻开历史的一页页,从中寻找发展的答案,洞见未来的方向。约十年前,我离开本已熟悉的地方,逆西江而上,到陌生的德庆去寻觅自己的路。在那个同样是西江边的山城,远离了城市的我得以在清凉安静、民风淳朴中安放下躁动疲累的身心,重新出发。在这里,如何更好更快地融入这方水土,我想到了地方志。在翻阅那厚重的《德庆县志(1979—2000)》时,我不禁为自己当初的选择庆幸,原来所到之处,并不是偏远闭塞、贫瘠落后,而是历史悠久、物产丰盛、人文荟萃。对于有志写作的我而言,这里又是一个“富矿”。
在基层的五年,我走进广阔的田野、原生态的乡村、淳朴的山水,从事的新闻采编工作在真实地记录此地的同时,也在记录自己平凡但丰富的人生,并且,在记录中发现了一些鲜活、动人、值得书写的题材。
2019年初,当我决定整理在德庆奔走几年的采访资料形成“西江”这个专题时,面对这个庞大的题目和众多的线索,我一下子陷入了两难,既不甘心放弃,又觉无从下手。这时候,我又想到了地方志。对于西江,这条南方的重要大河,地方志一定有着很多的记载。于是我隔三岔五地向县地方志办跑,在借阅的志书中搜寻我需要的关于西江的一切。无论是《德庆文史》《康州古色》《西江风情》,还是《德庆旧事》《德庆风物记新编》《康州杂记》,里面记载关于德庆的历史、人文、风物,都多少涉及西江。找寻的同时我也大有所获,连德庆边边角角的事物都了解得比一个德庆当地人要清楚了。
但是,对于西江的了解,不能只囿于一个地方对西江的记录,而应该在更广的角度、层面上去了解,这样才够全面、丰富。于是,我利用周末的时间,不仅访渔村、问疍家、上航船、走西江……还专程跑到肇庆地方志办,希望能找到有关西江的更专业、更全面的记录。果然,在肇庆市地方志办,工作人员了解到我是为着写西江而来,热情地为我作了指引并提供了相关材料,如《广东省志·水运志》《广东省志(1979—2000)·交通卷》《肇庆古驿道选辑》等,这些对西江详实记载的专业书籍,使我对写好西江这个题目平添了信心和动力。就这样,在资料堆中爬梳,在工作之余整理材料,不知不觉间,为着写西江这部专题散文集,我所查阅的地方志书、所参考的地方文献多达40余种。这些资料,除了到地方志办翻阅抄录,我还跑到图书馆借阅,甚至上孔夫子旧书网购买。如此,只为这个专题更详实,留下的遗憾更少一些。

蓝色西江(来源:西江日报社)
2022年2月,历经三年披沙沥金般的写作,目前国内第一本介绍西江流域风情、人物、渔俗文化的专题散文集《守河者》出版了。可以说,如果没有扎实的地方志资料作基础,光是靠着想象和抒情,是难以以点带面地勾勒出西江的丰富和博大。正是由于有坚实的地方史料为依托,我的书写才更具有脚踏实地之感。
在完成这部西江专题散文集后,本以为我与地方志的关联要告一段落,可没想到的是,某次我在翻阅《肇庆市人物志》时,忽地看到家乡的“革命烈士名录”上面竟然有曾祖父的事迹介绍。虽然是短短的两行,但对于此前只知道我们是革命烈士后人,至于他几时参加革命,当时的身份、职务,以及何时何地牺牲,我们所知甚少。激动之余,我将记载这页拍照发上家族微信群,大家都很感慨,没想到地方志记载得那么清楚,这是永载史册的珍贵记录啊。
地方志是对一个地方的发掘与书写,我们应如何发掘这个宝藏,展开个人的书写,我不禁陷入了沉思。
(作者单位:肇庆新区管理委员会科创工贸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