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8月,广东省自然村落历史人文普查资料全集《全粤村情·佛山市高明区卷》印刷出版,2021年10月出版自然村落历史人文普查成果开发利用系列丛书《高明区自然村落历史人文概况》,内容涵盖类目丰富,全面反映高明区540个自然村现存可查的历史人文状况,是对高明区自然村落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地毯式抢救性深入挖掘的重要成果。
笔者亲身参与调查和编纂两书,历时6年,查阅文献种类多、引用史料范围广;在编辑和校审文本时,发现以往编纂的地情书籍,部分内容存在不足与谬误的情况,造成了引用和参考编纂其他文本时盲目跟从,以高明区自然村落历史人文普查为例,提出以下几点愚见并简单举例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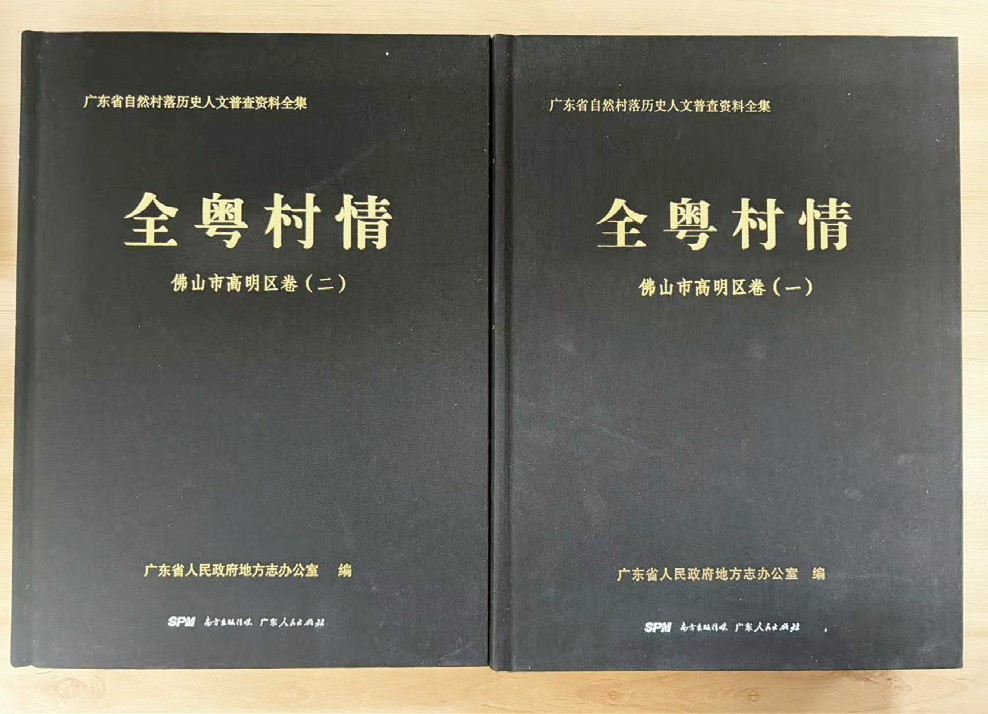
《全粤村情·佛山市高明区卷(一)(二)》
一、编纂文本以实事求是为原则
“实事求是”是严谨的治学态度,是编纂地方史志的原则,在编纂文本的时候,要掌握充分的事实理据,从事实中找出真实的结论。其关键在于掌握各方面的史料,支撑论点。因此要利用历史文献、档案实物、遗碑等有价值的史料,综合运用二重、三重或多重证据,寻绎有规律的事实理据。
在编纂过程中,忽略史料真实性的存在,盲目跟从所见资料照搬照抄,是编纂地方志的大忌。以清光绪二十年(1894)《高明县志》点注本为例,其附录的原高要县泰和乡资料(摘自《高要县志》①②)的姓氏考,所记的开族时间、源流、迁徙等内容,与现存各氏族旧谱本、遗献、遗碑所记大相径庭,但《高明市西安区志》③在编纂时,原文只字不漏,照搬录入,而现今此片区的族谱编修、村史介绍、网络宣传都有取材于此,造成重蹈覆辙的不良影响。
二、田野调查获取有价值的史料
田野调查,是实地进行调查的工作方式,有助于开拓视野,不被现存资料所局限,填补史料空白。开展自然村落历史人文普查,是田野调查方式的体现。高明区在田野调查中,以遗碑、遗献搜集的资料最为可贵。诸多遗碑多被填埋、涂抹、弃置,其中有庙宇碑记、祠宇碑记、坟茔碑记等50余通;遗献有著作、谱牒、契约等500余份,将其摄影或数字化。这些田野调查所获得的资料,用于修正与填补《高明县地名志》④的地名由来、村庄介绍,以及确认《高明文物》⑤建筑年份、录入遗漏等提供了实物证据。

2016年作者(左二)到自然村落普查调研
三、对有异议的史料举证与分析
分析现存的史料,会出现异议的情况,有时模棱两可,甚至引发纷争。研究对象存在有异议的,列举现存的史料要有针对性,从史料上根据理证、书证、物证、旁证等,通过归纳、比较、分析,运用逻辑推理方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科学的结论。对于不能下结论的,将有异议的说法并列以存,以待详考。在查阅高明宋儒谭惟寅墓葬位置、明进士谭彦芳的籍贯、清进士陆仁恺(又名仁恬)科考年份、水利工程金钗陂建筑年份等,因记载各有所本,载录不一,造成存在异议,通过列举志书、碑记、谱牒、遗文等一系列史料分析,得出造成异议的原因,还之以真实。
四、对有价值的史料须系统整理
史料按表现形式分为实物史料、文献史料、口述史料、影像史料;按照史料价值的不同,可分为原始史料、间接史料。原始史料一般为实物史料、影像资料,间接史料一般为文献史料、口述史料、影像史料(纪录片)等。除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馆藏的史料外,民间仍然存在大量的实物史料、文献史料,如高明区内存有中华第一报人梁发《日记言行》⑥、遗碑石刻、家风家训、谱牒名录汇辑、诗文汇集、历史故迹等民间丰富的历史资料,须系统整理。除此之外,口述历史,趁有可述之人在,应刻不容缓进行采访整理。整理时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要体现学术价值、资料价值、宣传价值、教育价值,使之应用于社会。
一方之史存之以真实,不仅为众多领域的研究提供素材,为延续历史文脉提供事实依据,同时也为政府及有关部门的相关决策提供基础性的资政信息,对推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注:
①马呈图等纂修:民国《高要县志》,1938年铅印本。
②梁赞燊等纂修:民国《高要县志》,1948年油印,1973年重刊本。
③陈汉权主编:《高明市西安区志》,2003年版,第70—75页。
④《高明县地名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高明县地名志》,1992年。
⑤《高明文物》编辑委员:《高明文物》,2009年。
⑥梁发手书,清道光十年(1830),《日记言行》,高明区档案馆藏影印本。
(作者单位:佛山市高明区地方志办公室)







